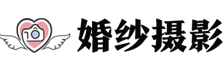mile米乐m6东风村的李金兰与回乡探亲的杨厚恩在亲戚介绍撮合下相识,短暂相处后两人决定结婚,男方送来的聘礼是
虽然婚房窄小得只能放下一张双人床和一个二屉柜橱,但新生活的希望已在瓦片覆盖的简陋屋檐下悄然萌发。尽管经济条件有限,但这场婚礼的仪式感却丝毫未减。“他后来给我买了件结婚当天穿的红色新外套,”李金兰回忆说,“那时没有现在这些隆重的梳妆打扮,我只是提前烫了个头。”
与那个年代的无数普通工薪家庭一样,李金兰的婚礼简朴却充满浓厚的人情味,当时的送亲场景令她记忆犹新:“甭管痰盂、暖壶,还是脸盆儿、花瓶,亲戚朋友们一人举着一样,热热闹闹排着大队就出发了!”
除砖厂同事随了五块钱礼金,其他亲友和街坊四邻送来的贺礼,多是暖壶、脸盆架、被面、毛巾、枕巾这些生活必需品。“大家送的东西真不少,到现在还有两个脸盆儿我在用着呢。”物质匮乏并未消减人们之间的温情,“虽然不富裕,但我挺知足的。”这份亲情温暖让李金兰至今回味无穷。
1977年,当嫁到东坝的赵丽敏乘坐的婚车——北京吉普驶入三岔河村时,围观村民眼中闪烁着惊奇的光芒。在自行车是主流交通工具的年代,这辆由公公单位协调来的汽车无疑成为当时罕见的奢侈品。对新娘赵丽敏而言,这辆车不仅载着她驶向婚姻之路,也开启了她作为“东坝媳妇”的人生新起点。
赵丽敏的爱人也是当时返城的下乡知青之一。城市里住房紧张,为了安顿新人,婆家在老家三岔河村紧急赶工,仅用三个月时间便盖起了三间瓦房。虽然婚礼临近时,只有一间房装好了门窗,但床、柜子、桌椅板凳连同火炉和厨房用具均已备齐,用公公的话说“进门就可以做饭”,一个新家庭的雏形总算有了着落。
婚礼当天,赵丽敏身穿喜庆的红上衣、蓝裤子,两条乌黑的大辫子垂在肩头。疼爱孙女的奶奶用头绳将她的辫尾仔细卷起,寄托着“夫妻长久”的美好寓意。
仪式遵循东坝婚礼的传统流程:婚礼当日上午接亲,中午在男方家(即三岔河村的新房)正式宴请。宴席摆了4桌,款待的都是至亲,炖肉、豆腐、丸子、肘子、鸡、鱼等丰富菜肴热气腾腾,饱含着浓浓的乡土情谊。
这场婚姻的缔结,同样深深刻有上世纪留下的特殊印记。领取结婚证时,双方须持各自单位或生产队开具的介绍信。据赵丽敏回忆,介绍信上工整地写着:“我村女青年赵丽敏,已到结婚年龄,自愿与巴文生结婚。”这张薄薄的纸片,成为当时的人们通往婚姻殿堂不可或缺的通行证。
她与爱人的婚姻是经自由恋爱后结为连理的。两人原是同事,在众多追求者中,刘彦霞认真地选择了现在的丈夫,“因为他人品好、不自私”。由于工作单位紧邻朝阳区文化馆,看电影成了他们主要的约会方式,“一张票才几毛钱,那会儿没少进影院,《简爱》《卖花姑娘》我们都看过。”
恋爱几个月后,两人决定结婚。双方父母见面时,男方按照东坝习俗带了烟酒茶糖和点心等几样盒礼,“家长都很开明,只要孩子们乐意就行。”
婚期商定后,准新娘刘彦霞收到了男方家庭的一份心意——500元“买衣服钱”,这笔当年“可观”的数目足够让她在前门的新新服装店添置一身西装、一件呢子大衣及其他衣物。
不仅如此,男方家将自家五间正房的其中两间用作他们的婚房,屋里摆着齐全的各式新款家具:双人床、大衣柜、写字台、高低柜等一应俱全。上世纪80年代,结婚流行“三转一提溜”,包括自行车、手表、缝纫机,还有时髦的录音机。
女方家也没少张罗嫁妆:一个滴答作响的555牌座钟、一套款式时髦的沙发、两只喜庆的红皮箱、新做的几身衣裳,还有一盏照亮新生活的落地灯。这两间房里被塞得满满当当,装满了双方家庭对新婚夫妇的美好祝福。
婚礼当天最显眼的,还是三辆军绿色的北京吉普接亲车,这在当时足够体面,也彰显出东坝婚礼习俗的新气象。“那会儿不兴穿婚纱,也没人给化妆,”刘彦霞笑着说,“我就把头发梳了个利落的马尾辫。”妆容虽然朴素,却透着新时代新人特有的精气神儿。
新娘子接走后不久,娘家的亲戚们就该动身去“瞧酒”了,也就是去新姑爷家看望新人。大家都会自带一个点心匣子作为随手礼,男方则根据提前告知的人数预留宴席款待。这一习俗既保留了东坝婚庆的传统礼数,也延续了婚礼喜庆氛围,满满的人情味儿就在你来我往、推杯换盏的欢笑热闹中暖暖流淌、接续传承。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作为农村地区的东坝婚宴,宛如一幅鲜活且充满烟火气的民俗画卷,承载着浓浓的乡情和厚重的心意。
据后街村党支部书记宋志杰回忆,婚宴的席面都是在自家院子里搭棚,厨子则是同村街坊邻居。老汤肘子饭馆的创始人刘崇林,正是那个年代活跃在乡村婚宴舞台上的“灶厨”代表,因为一手好厨艺,七棵树大队下辖六个自然村的“红白事儿”,基本都会请他带队帮忙“灶厨”,甚至外村也有不少人家拜托熟人邀他前往。
据刘崇林的儿子刘阳和徒弟王立东共同回忆,东坝婚宴席面上的菜品丰富多样,有香酥鸡、红烧鲤鱼、炖肘子、炖肉豆泡儿、汤丸子、清炒鱿鱼卷、红烧海参、拔丝白薯、酱瓜丁儿、金糕梨丝……最后压轴的主食,必定是一碗热腾腾的打卤面。从前农村把参加婚宴又叫做“吃喜面”,足见其重要性。
在东坝,根据接亲日期的不同,传统婚庆喜宴通常要办两至三天流水席。第一天“落(lào)作儿”比较简单,主要是招待帮忙的人。一早,帮忙的乡亲分成几组,各司其职:有的去建筑队借架子管、帆布搭喜棚;有的挨家挨户借桌椅板凳、盘碗杯碟;还有一组人马专门负责和泥搬砖,在院子里搭起炒菜、炖肉和煮面的三口大灶。大厨则领着本家到市集上选购食材,回来后便是择、洗、切、炸、炖、煮,做足准备工作。
不管接亲是哪天,正式招待宾朋一般是在第二天,这是灶厨的“重头戏”。正席一开就是6至8桌,一桌宾朋吃完立马清一桌,待所有桌都清完并坐满下一轮的宾朋后就又开一轮。后厨帮忙的街坊大妈们则迅速将撤下的碗碟洗涮干净,以备使用,如此流水往复。宋志杰回忆说:“最多的要安排四五轮,经常上午10点开始摆桌,下午1点半还有没上桌吃饭的呢。”
在宴席临近尾声时,灶厨的大师傅会亲自端上一盆汤,这时,懂礼数的娘家人就会立刻送上两个“汤封儿”红包,以表示对灶厨人员辛苦工作的感谢。师傅们收到“汤封儿”后也不揣进自己兜里,拿出来买几盒好烟,与后厨帮忙的乡亲一起分享。
在常青藤第二社区的居民马民柱、石会家中,至今还保留着1995年二人结婚时的照片和录像,闲暇时他们常会翻看观赏,让思绪飘回三十年前充满幸福的那一刻。
结婚前,公婆给了石会3万块钱用于置办婚礼物品——新衣、家具、首饰等,这笔礼金远超当时1万元左右的平均水平,足以显示婆家对她的重视。夫妇二人从中拿出1800元钱,拍摄了一组时髦的婚纱照,引来不少同事艳羡的目光。
结婚当天,石会的妹妹特意托关系找来5辆奥迪车组成迎亲车队。尽管两家离得很近,车队依然浩浩荡荡地驶入小区,绕行一圈后才将新婚夫妇送至婆家,仪式感十足。“一辈子就这么一次,绝对不能留下遗憾。”石会满意地回忆着当时的盛况。
翻看当年的结婚照片,依然能感受到现场的喜气:马民柱西装笔挺,精神抖擞;石会则身着精心挑选的粉色婚纱,盘着高高的发髻,妆容明艳动人。
这身造型来之不易,是她一大早就赶到理发店特意做的,照片大多由拥有相机的亲友们抓拍记录,更难得的是,妹妹还专门请来了摄影师,为姐姐录制了珍贵的婚礼现场视频。
石会格外珍视这些记忆。随着科技发展,她把录像带转录成CD光盘,如今又琢磨着要把它们存进U盘永久保存。“人生的重要时刻,就要给自己留个纪念。”她这样说道。
这份对仪式感的坚持也延续到了下一代——2023年,当儿子儿媳提出去云南旅拍婚纱照时,石会立刻表态支持:“去!妈出钱!”看到孩子们唯美的旅拍照,她的喜悦甚至超过了新婚的小两口。
2005年,当赵丽敏的女儿在东坝大鸭梨饭店举办婚礼时,东坝这个曾以流水席为主的京郊地区,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消费升级。“我选的是最好的套餐,亲戚朋友反馈说,‘吃过那么多次婚宴,您家的菜色最好!’”她开心地回忆道。五年后,儿子的婚礼更进一步——红太阳生态园的玻璃穹顶下,在绿植环绕的清新氛围中,满满二十桌宾客尽情享用着海参与烤鸭等精美佳肴。
2013年,刘彦霞儿子结婚时,婚礼筹备已形成完整产业链:从选购婚纱礼服,到拍摄万元级婚纱照,再到婚庆公司提供的“四位一体”服务(策划、主持、化妆、摄影),整个流程宛如流水线作业。红色敞篷跑车成为接亲头车,婚礼现场聚光灯取代了日光,婚庆公司搭建的舞台如梦似幻。
新娘与朋友在专业音响中献上排演数周的舞蹈……当新人第二年才补上蜜月旅行时,婚礼已从“过日子”的起点,蜕变为一场值得精心编排的人生大秀。
时光倏忽而逝,2025年的今日,东坝新人大多选择在落成不久的万达锦华酒店举办婚宴,华丽气派的大宴会厅中,洁白的席面依次延展开来,质感精美而细节繁复的改良版汉服取代了婚纱,排成长队的豪华婚车则换成轻便时髦的共享单车车队;宾客伴手礼升级为定制新人签名或漫画的书签、糖盒等文创,而婚礼全程多机位跟拍,新人们亲自剪辑的秀恩爱小视频总会逗引出亲朋好友抑制不住的激动泪花……
当物质需求得到充分满足,情感联结与文化认同就成为新一代群体的核心诉求。Z世代新人们想要的,更多是“参与感”而非“观赏性”,这种巨大的转变背后,是智能新时代里年轻人对婚姻本质的重新定义。
回望东坝六十载婚俗变迁,一条通向幸福的主线清晰可见:婚礼的操办权,经历了从集体到家庭,最终回归到新人自己手中的历程。上世纪七十年代,家长意志主导着青年们相亲的节奏,父母之命仍颇具分量。而今天,婚纱照取景地的选择、蜜月行程的安排,婚礼风格决定权已完全交由新人。
新人们看重的婚姻内涵也正在不断打破重塑。刘彦霞当年选择对象时最看重“人品好,不自私”,而今天年轻人婚礼上播放的恋爱纪录片里,“共同爱好”“灵魂契合”成为高频词。从“搭伙过日子”到追求精神共鸣,物质丰盈之下,婚姻的意义也向灵魂更深处继续探索。